| 最高人民检察院 | 正义网 | |
|
网站无障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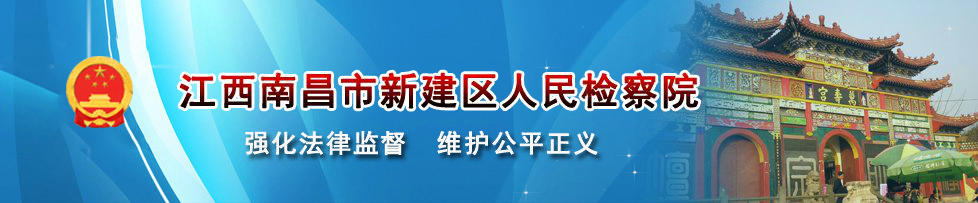 |

“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苏北盐城,丹顶鹤的故乡,一个叫徐秀娟的女孩,为救丹顶鹤献出了年仅23岁的生命,一个真实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我的家乡就在那里,在那河网密布、芦苇丛生的射阳河畔。芦苇,那么地随处可见,也易让人对其视而不见。后来读书,《琵琶行》开篇:“枫叶荻花秋瑟瑟”,荻花就是芦苇花,在被贬、送别的大前提下,我想象并感受着作者眼前的景象:萧瑟的秋风、白茫茫的芦苇花,一如风中飘摇的蓬草,让人心情跟着沉重不已。再后来,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中引用了一句“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更是让我觉得芦苇与反面形象形影不离。直到学习《诗经》中的《蒹葭》一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当我得知蒹葭就是芦苇时,惊讶不已,多么诗意美好的形象!同样是在秋天,而且是深秋,意境完全不一样,一切都是因为爱情元素的加入。我随后也发现,芦苇也有开紫色花的,沾上了一点高贵的色彩。再后来,读到帕斯卡的“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芦苇已经被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哲思的对象了。我在体会这句话的深邃与精妙的同时,也总在想:如果牛顿是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中受启发而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那么,帕斯卡这支芦苇肯定在芦苇深处穿梭过很多次。动画片《千与千寻》中主人公千寻的全名叫荻野千寻,如果把“寻”作为亩之类的度量单位来理解的话,那就是一片碧波起伏上的白紫相间的芦苇花海,美丽的名字。如果把它作为寻找来讲,则暗合影片的教育意义:面对困境,我们不仅需要有思考的能力,更需要有足够的意志和方法去找寻通往生活的道路与回归生活的力量。
离开家乡十几年,入诗入文的芦苇再次被我遗忘。今年端午回家,我在姐姐的带领下包起了粽子。氤氲的粽香之中,我笨拙费力地包着粽子,关于芦苇的记忆也一点点浮到眼前。
早春时节,蒌蒿满地芦芽短,不出几日,芦苇便冒出水面,像绿箭一样噌噌地往上窜。小学的路上,男生随手摘一片芦苇叶,卷成哨子吹起来,或呼朋引伴或独行作伴,低沉的、清脆的,长长短短,简单快乐。
等到我学数字的时候,母亲便用芦苇杆给我做成“小棒”来帮助我,选细细、白白的芦杆,切成一样长短,用针线串成一串。老师教十以内的数字的时候,那一串便是十根,教二十的时候,再做一串二十根的,直到一百。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固然不能演绎画荻教子的故事,但是,每次她在灯下给我串小棒都是那么认真,眼神又是那么地柔和,充满希望。
到了立夏,芦苇已经长过人高,叶子也基本长成,弯垂下来,像一个安静的青衣姑娘。家乡的立夏比端午隆重,吃粽子是习俗之一,立夏时节的芦苇叶也是最鲜嫩的。用芦苇叶包粽子是一项技术活,成了考验姑娘家心灵手巧的标准。为了不浪费糯米,母亲让我用泥土代替糯米来学包粽子。泥土包的粽子更加不像,反而像一把小手枪,于是我和小伙伴们不一会儿便拿起粽枪打起仗来。还有人折来芦苇,把顶端芦苇叶用指甲划成细细的穗子,做成一把“红缨枪”来参战。我们学着露天电影里看到的一点镜头,扮演角色,互相打杀,玩多少次都不过瘾。
小满后的一个多月,是割麦插秧的农忙时节,芦苇叶又有了新的用途,当做茶叶煮水喝。父亲在地里干活总是顾不上吃饭喝水,所以母亲得空便煮一锅芦苇茶,让我们送到地里给他喝。芦苇茶汤色清亮,清香扑鼻,甜美滋润,父亲咕咚咕咚几口就把一缸茶全部喝完。
每年八九月间,芦苇便开始抽穗开花,芦穗油亮润泽,摸在手里贴在脸上很是舒服。有一次,我问父亲:芦苇没有吃油也没有吃肉,怎么穗子这么油亮呢?父亲听了默不作声,我猜他是不知道,便故意追着他问,父亲最后回答说:你妈年轻的时候,长头发又黑又亮,不也没吃过什么油和肉?文不对题,我当年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若干年后,看到电视上洗发水的广告时,女主角的长发掠过男主角的脸庞,父亲的回答便有了意义。
霜降过后,芦苇渐渐发黄变枯。地里庄稼全都侍弄好了以后,一向停歇不下来的父亲,便开始用他自制的长柴刀割芦苇。寒冬腊月,一般人家都不会去割水里的芦苇,但是向来俭省认真的父亲却每年都要进到水里把芦苇割得干干净净,并且割了几十年。每次收工,他的裤子和鞋子里都是水,走起路来,扑哧扑哧……灰黑的夜色中,我默默地跟在父亲身后,冬天干冷得发白的路面上留下一串黑黑的湿脚印……
割下来的芦苇在河滩上晒干后,长的齐整的做成席子,短的细的打成帘子,芦苇梢头做扫把,芦苇花编成“毛窝子”当鞋穿,还可以编成畚箕、篮子等等各种盛器和用具。环顾屋子,到处都有芦苇的身影。
芦苇在家乡那里一直被叫做芦柴,简称柴,与“才”、“财”同音,是好东西。起房子的人家多会选购上好的柴用细麻绳扎成粗粗的“财子”横担在人字形的梁上。不知道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学会扎“财子”的,反正每次瓦匠队到哪家起房子,大多会推荐房主来请他,父亲便会带上母亲去给人家做。扎“财子”的地方一般都比较空旷,需要有足够的地方伸展和摆放二十多米长的“财子”,所以,很多时候选在晒谷场上。父亲到了场地后,便开始在起点、终点和扎财子的地方打桩定位。他没有带尺子,背着手跨几步,便知道在哪里打桩了。在梁宽一定的前提下,“财子”的长度、直径和数量也要一定,二十多米的财子必须粗细均匀,在没有测量工具、芦苇长短不齐、粗细不均的情况下,父亲全凭经验和手感。这一把要抓几根,下一节要添几根,父亲时刻在估算着,母亲也步步紧跟,密切配合。就这样,为了赶在“上梁的好日子”前完成工作,每天从天蒙蒙亮开始,一直到黑得看不见,他们在没有任何遮挡的晒谷场上,一刻不闲,一力不省,不管风吹日晒,不管严寒酷暑,扎遍了十里八乡。
初中之前,每到冬天,村里经常会有“挑河工”的任务。其实就是国家为了修渠、修路等大型工程,分派给农民的义务劳动。苏北有太多的河、沟、湖、荡,为了灌溉也为了防洪,必须修整。“挑河工”通常都是交换进行,我们村里的人会被带到外地,外地人会到我们这里。我家住过好几批外地河工,有专门的人做饭,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吃大锅饭,中午还能吃到肉,所以,我觉得挑河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同时,河底的芦苇根被挖了出来,白白嫩嫩甜甜的,洗了就可以吃,成了我们的零食,上学放学,书包里总要塞几根。既有肉吃又有“零食”吃的我们,全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父兄在远处,干着超出人体负荷的劳动,哥哥几次坚持不下来跑回家,瘦得像芦苇一样的父亲在那里加倍地挑着,挖着。寒冬腊月,他们光着脚,弯着腰,一锹锹挖,一担担挑,没有挖机,没有运土机,全靠人力。芦苇蔓延的根茎,一如父亲腿脚上突起的血管筋脉,又像母亲对父兄的担心、牵挂和思念,在没有通讯工具、没有父亲任何音信的情况下,每到傍晚,她都要站在屋后的路上,用力地听着、看着远处的行人和行路声,一任寒风吹起她芦苇花絮般过早花白的头发。
说到全身是宝,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莲,它是城里人养生养性的宝。莲很美,让人不愿意她有一丝的不完美,看到她东倒西歪便心生不忍。等到秋冬,残荷败叶,枯缩凋零,与夏季的鲜妍极盛反差太大,让人感慨伤神。芦苇则不同,风中、雨中、雪中,即便是孤身一支在水中央,也绝不东倒西歪,永远保持正直挺立的姿态,宁折不弯。苇叶也只是从绿色变成枯黄色,既不枯缩变形也不枯死变黑。如果是丛生的芦苇,更是比肩挺立,密生成阵。它们不需栽植,不需施肥打药,不需任何的人工管护。勤劳聪慧的苏北祖先,在生产生活中,将上天赐予的芦苇的用处发挥到极致。可以说,芦苇也是全身是宝。根茎叶都可以入药,同样有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不蔓不枝、亭亭净植的正派作风;中空外直、虚怀有节的谦虚精神;用青衣白花、素面朝天书写它的纯粹质朴;虽然远离闹市、静守一隅但是又相依相伴、抱团合群。如果说莲是花之君子,是文人墨客。那么芦苇,便可以算是粗使丫鬟或者杂使仆役,是劳苦大众,务实、效用、出活是其首要使命。使用芦苇的人像对待芦苇一样对待自己、要求自己,人尽其才、人尽其力的同时帮助物尽其用,不负上天赐予我们的一切。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吧?
版权所有: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检察院 单位地址:江西省新建区长堎镇新建大道481号 本网网页设计、图标、内容未经协议授权禁止转载、摘编或建立镜像,禁止作为任何商业用途的使用。 |